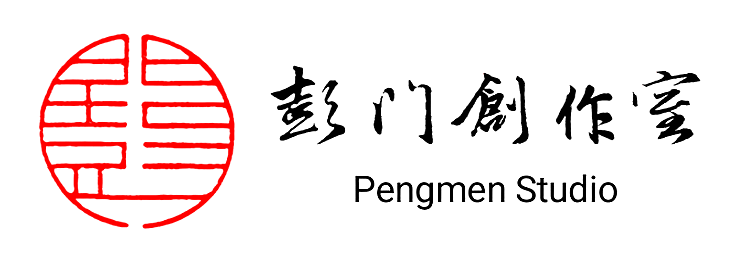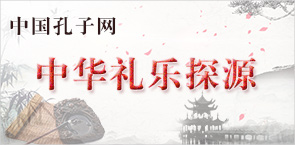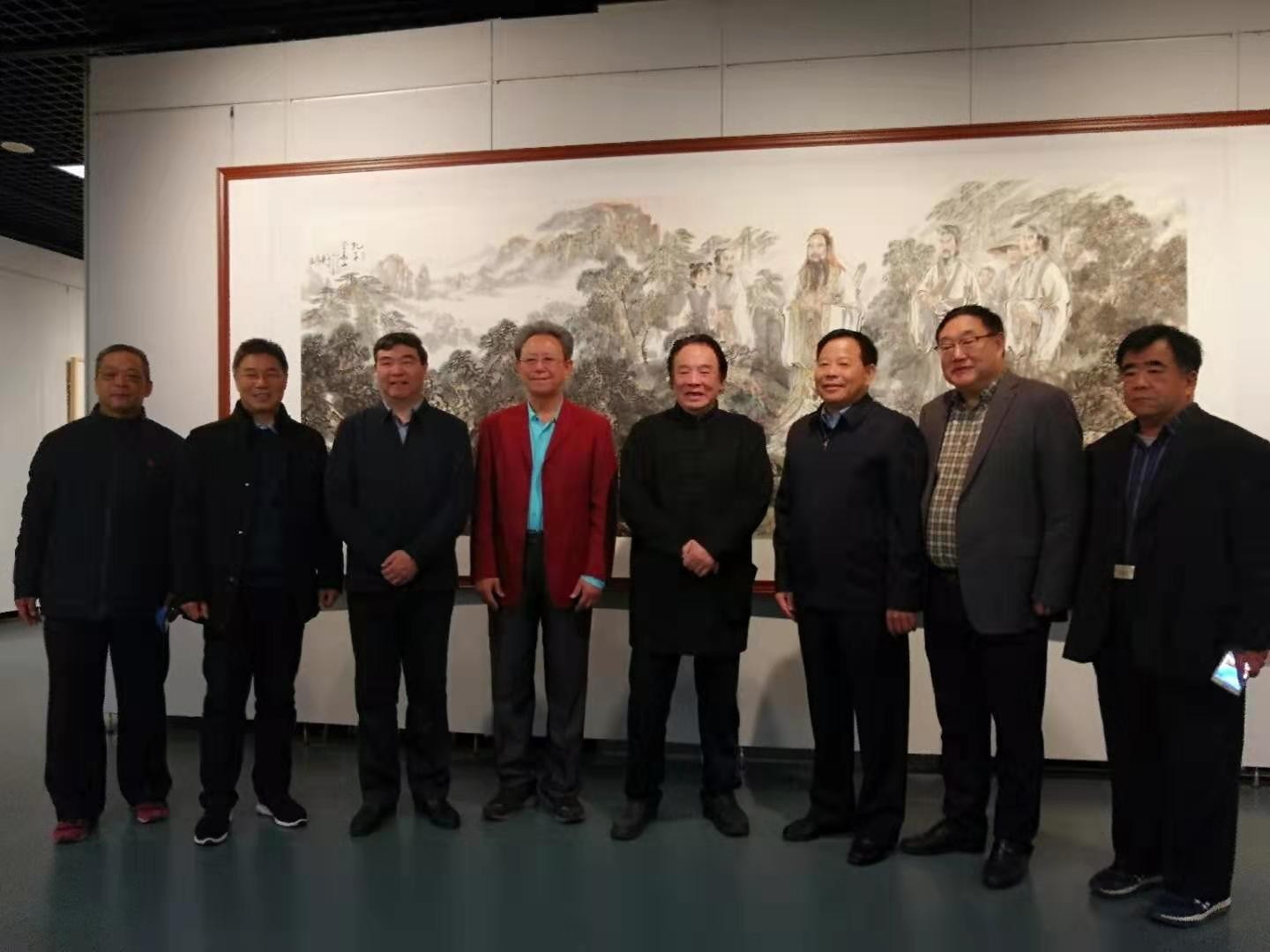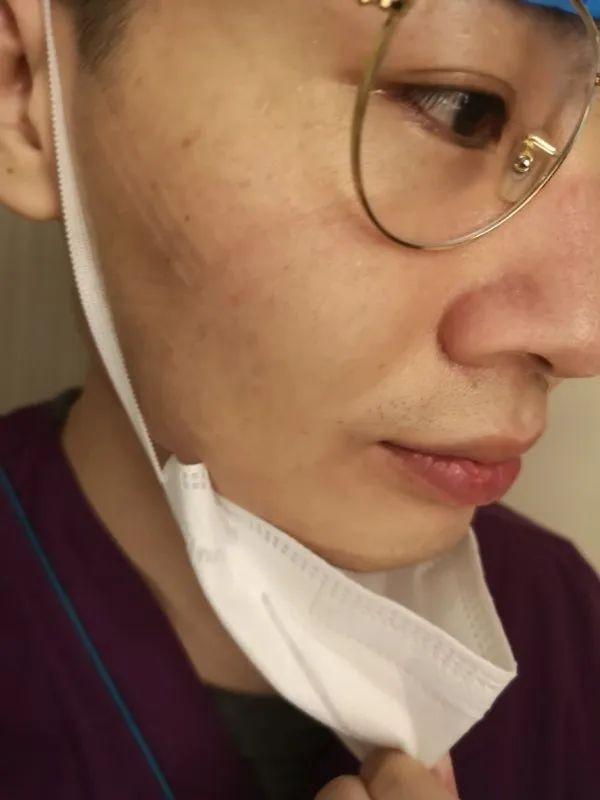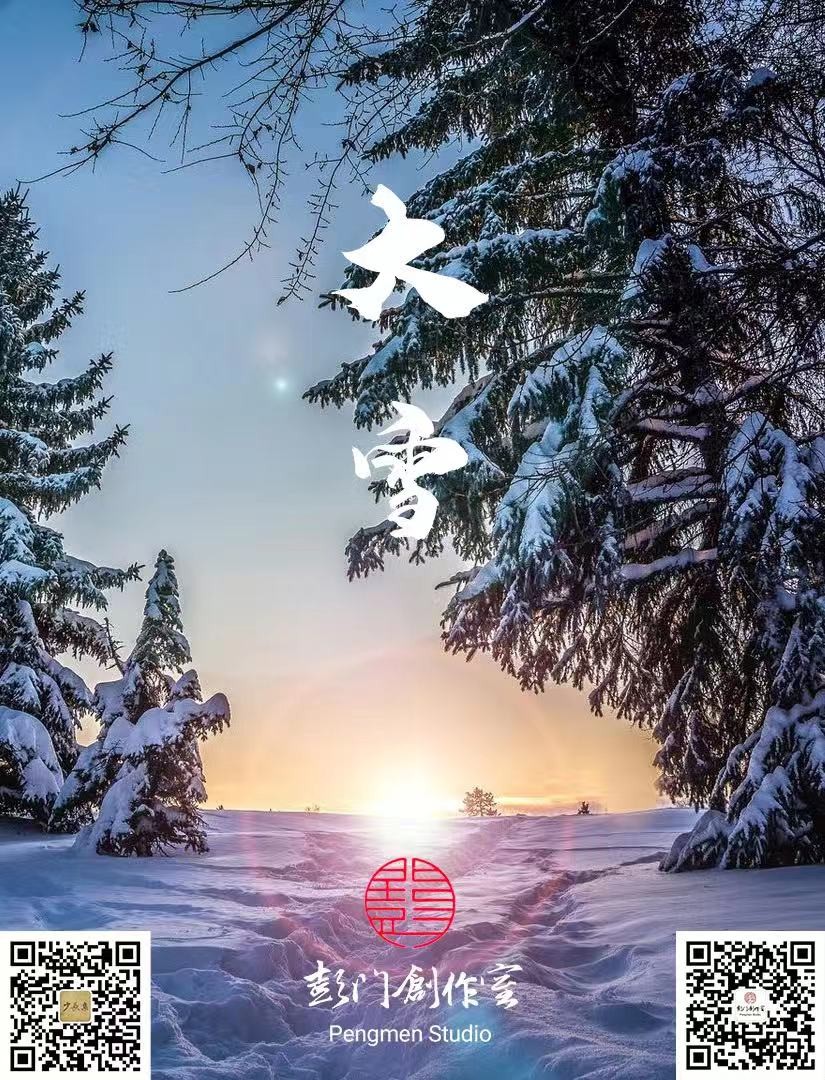魯國請回孔子為什么沒有任用
? ?
?
魯國請回孔子為什么沒有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孟繼新
?
?
????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魯國執政之卿季康子,決定請回流離在外的孔子。《史記·孔子世家》說:“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季康子派公華、公賓、公林,帶著禮物迎接孔子,于是孔子結束他的漂泊生活,回到了魯國。
????孔子55歲時開始周游列國,終于在68歲時返回魯國,四處奔波整整14年,歷經磨難,周游了衛、曹、宋、陳、蔡、楚大小近十個國家。他席不暇暖,到處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斷尋找機會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卻沒有一個國君肯重用他。相反,他和弟子們“削跡于衛,伐樹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吃盡了顛簸勞頓之苦。
魯國這次迎接孔子回魯,可以說是禮儀莊重,形式高調。按理說,孔子回魯后本應得到魯國的重用,不知為什么,孔子卻始終沒被任用……
為了一探究竟,我們還應從孔子回魯時的前前后后說起。
魯哀公十一年春天,齊、魯之間又發生了一場戰爭。齊國貴族國書等人率軍隊攻打魯國,到達清(今山東長清東南),季康子問計于冉求,冉求極力主張季康子親征,叔孫、孟孫氏從征。但叔孫、孟孫氏持異議。冉求分析了當時的情況,勸誡季康子:“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康子便讓冉求隨他入朝,經過爭議,最后結果是讓孟孺子帥右師,顏羽駕車,邴洩為右乘;讓冉求帥左師,管周父駕車,孔子另一位弟子樊遲為右乘;在冉求的指揮下,魯軍大敗齊軍。
戰爭結束后,季康子問冉求的軍事指揮才能是哪里來的,冉求告訴季康子,是從孔子那里學來的,于是,季康子決定迎孔子回魯。“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求曰,學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史記·孔子世家》)
雖然此時的孔子已年近七旬,但他的本性并沒有因為歷經磨難而改變。其性情老而彌堅、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季康子派人接回孔子,本想重用他,但是由于孔子并不支持田賦改革,就放棄了重用孔子的計劃。
原來,季康子想實行名為田賦的征稅方法,他派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見,孔子以不懂做答;冉求問了三次,孔子依然顧我。冉求說:“子為國老,待子而行,答之何子之不言也?”(《左傳·哀公十一年》)您是退休的卿大夫,對于這種國家大事,你為什么不發表意見呢?孔子私下對冉求說:“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人,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茍而賦,又何訪焉?”(《國語·魯語下》)君子辦事情,要用禮來衡量,施舍要多,辦事要適中,賦斂要少。如果這樣,按照原來的辦法也就足夠了。如果沒有禮來制衡,貪得無厭,即使按照新的田賦方法征稅也是無濟于事。季孫氏如果想合乎法度地做事,有周公的典章制度在那里;如果想隨意行事,又何必征求我的意見。
孔子一向反對加重人民的剝削,這次由于剛回魯國,因此沒有公開反對,只是私下表示了不同意見,當然他也希望通過冉求讓季康子知道自己的意見。但是,季孫氏聽不進孔子的意見,照常實行田賦法征稅。孔子很憤怒,由于他無法反對季康子,就責難幫助季康子的冉求,公開宣稱冉求不是他的弟子,鼓動其余的弟子羞辱他。《論語·先進》說:“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嗚鼓而攻之,可也!”孔子雖未正面和季康子發生沖突,但季康子知道與孔子不相為謀,因此不再考慮重用孔子。
從那以后,孔子對季康子不在報任何希望,他對季康子逐漸由私下不滿轉向公開批評甚至當面指責。季康子向孔子多次問政。第一次比較客氣,“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季康子問如何才能使人民嚴肅認真,盡心竭力、互相勸勉。孔子說,你對人民恭敬莊重,人民就會嚴肅認真;你孝敬父母、慈愛幼小,人民就會竭心盡力;你選用賢能來教育人,人民就會互相勸勉。
季康子又問孔子的弟子是否能從政的問題。“季康子問,仲由可以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以從政嗎?孔子說,仲由辦事果斷,處理政事是可以勝任的。又問端木賜是否可以從政?孔子說,端木賜通情達理,處理政事是可以勝任的。再問冉求能不能從政?孔子說,冉求多才多藝,處理政事也是可以勝任的。
季康子問,殺掉壞人親近好人怎么樣?“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孔子說,為什么您治理國家一定要殺人呢?您存心向善,老百姓就會一定向善。君子的品德就像風,老百姓的品德就像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
季康子又問如何使政治端正。“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孔子說,正直就是端正。您帶頭端正,誰敢不端正?
季康子問強盜太多怎么辦?“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窈。”(《論語·顏淵》)孔子直接指責他,如果您不貪財。就是獎勵他們,他們也不會去偷去搶。由于孔子總是批評季康子,又處處和他對抗,從此再也未能獲得重用的機會。
魯國不重用孔子,孔子也不想再從政。他清醒地認識到,在當時的環境下,自己的政治理想已不可能實現,他只能寄希望于弟子,寄希望于后世,所以他將晚年的精力全部放在教育和整理文獻上。
魯哀公十四年,魯國圍獵,打死一頭怪獸,孔子專門去看,認為是麒麟。麒麟是一種瑞獸,只出現在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時期,亂世出現就會被殺害。孔子悲傷地說,黃河里不出現神龍背負河圖,洛水里不出現靈龜背負洛書,我就離辭世不遠了。天下清平無望,孔子絕望了,連正在編寫中的《春秋》也停筆了。公元前479年4月,孔子生病,子貢前來看望。孔子正拄著拐杖在門口散步,他看到子貢就說,你怎么來得這么晚?然后長嘆一聲唱起了歌:“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孔子家語·終記解》)泰山就要倒了,梁柱就要斷了,哲人就要死了。淚隨歌下,然后告訴子貢做的夢;夏代人的棺材停放在東邊的臺階旁,周代人的棺材停放在西邊的臺階旁,殷代人的棺材停放在兩個柱子之間。我坐在兩個柱子之間接受祭奠,我原來是殷代人啊。孔子認為自己即將辭世。7天后,孔子就真的去世了。
孔子去世后,魯哀公親自為孔子致吊唁的誄詞:“旻天不吊,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左傳·哀公十六年》)子貢聽了哀公的誄詞后說:“君其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左傳·哀公十六年》)國君恐怕不會在魯國壽終正寢吧。老師曾經說過,喪失意志就叫昏亂,喪失名分就叫過失。活著的時候不能任用,死了以后才致詞悼念,這是不合乎禮制的。自稱“一人”,這是不合乎名分的。在這兩方面國君您錯了。事實證明子貢的判斷的準確性。11年后,魯哀公被三桓驅逐逃往越國,在那里客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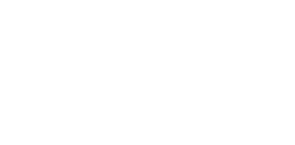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手機:13863756448 郵編:27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