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jìn)退有節(jié),舉止有度——關(guān)于坐、立、行的禮節(ji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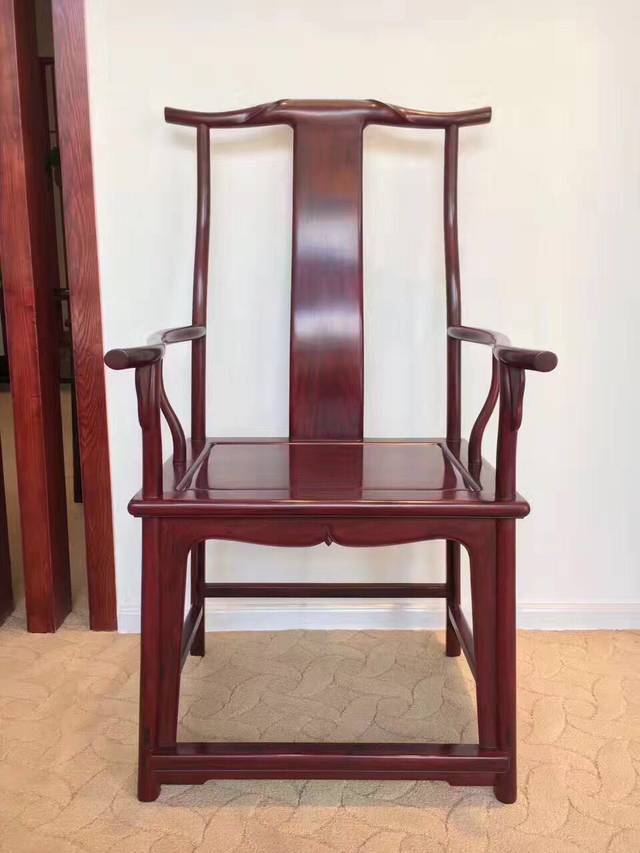
作者:彭慶濤 孟祥明 劉歡 ????來源:彭門創(chuàng)作室
中國是傳統(tǒng)的禮儀之邦,無論國家政治、人生歷程、日常生活,處處存在著禮俗的節(jié)制,這些禮俗不僅是維護(hù)著社會秩序,更是內(nèi)化于心,融入在人們的一舉一動中。在這樣濃厚的禮儀氛圍中,人們各種身姿體態(tài)亦有著相應(yīng)的禮節(jié)存在,所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便是對此的形象解釋。
一、關(guān)于坐的禮節(jié)
古人的“坐姿”是很講究的,門類也不少。同一個坐姿,也有不同的“坐法”。有關(guān)坐姿的要求,古人稱之為“坐容”,系“容經(jīng)”的組成部分。西漢賈誼在《新書》中專門寫了《容經(jīng)》一章:“坐以經(jīng)立之容,胻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jīng)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nèi)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就是身體挺直了坐下,小腿不要伸得一長一短,腳掌不要著地。兩眼平視的,稱為“經(jīng)坐”;頭微低,目光注視對面尊者的膝蓋,叫“恭坐”;低頭,視覺應(yīng)在自身周邊不可太遠(yuǎn),稱為“肅坐”;垂頭目光看地,手肘下垂,為“卑坐”。賈誼所說的“經(jīng)坐”,其實(shí)就是常規(guī)的“安坐”,即“席地而坐”。其實(shí),賈誼的《容經(jīng)》是專為諸侯王而寫的“禮儀教材”。可見,“怎么坐”在當(dāng)時確實(shí)很重要。
坐的姿態(tài),首先是一種禮,然后才是一種儀。漢代以前,在正式場合人們大多是席地而坐,其坐姿是雙膝跪地,小腿平置,臀部自然地貼于腳后跟處。而在嚴(yán)肅時,身體要挺直,眼睛平視,此坐姿叫“平坐”,或叫“正坐”“安坐”。下級對上級,頭應(yīng)微低,此坐姿稱之為“危坐”。
在唐宋以前,由于沒有桌椅,或者說桌椅沒有普及,人們就在地上鋪一張大席,就叫做“筵”,再在筵上鋪一張略小的席子,叫做“席”,那么人其實(shí)就是坐在席上的。古人在登席之前要脫掉鞋子,然后雙腿跪坐在席上,這樣的坐姿是正式場合中最恭敬規(guī)矩的姿勢。
除了“危坐”,還有一種坐姿就是“跽坐”。“跽坐”是直立上身,這樣的坐姿比起“危坐”更加隨意,一般是上級對下級的坐姿,也是表示一種尊重。如《戰(zhàn)國策·秦策三》載:“范睢至秦……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jiān)唬骸壬我孕医坦讶耍俊额≡唬骸ㄎā!虚g,秦王復(fù)請,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危坐”和“跽坐”,時間長了,腿部容易發(fā)麻發(fā)木,而且筵席凹凸不平,很容易硌得人腿疼屁股疼。即使知道這樣的坐姿不舒服,也只能忍受。除了這兩種坐姿,還有“蹲踞”和“箕踞”,此兩種多是在非正式場所或雙方熟知情況下的坐姿。“蹲踞”就是臀部著地,雙腿并齊自然彎曲,雙手抱膝而坐。這種坐姿其實(shí)今天還是能夠見到的。“箕”說的就是“簸箕”,所以,“箕坐”就是如簸箕一樣坐著,臀部著地,兩條腿伸直而坐。
二、站立的禮節(jié)
我們首先從《禮記·曲禮》中,看看古人對“站立”的要求:
“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立必正方,不傾聽。”
“室中不翔,并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此大意是說:
游走時不可表現(xiàn)出傲慢的樣子,站立時不可有一腳歪斜,坐著時不可雙腿大開像簸箕,睡覺時不可趴著睡。
坐,要坐得像尸一樣端正;站,要站得像祭祀或典禮一般恭敬。
餐飲之際不坐中間,走路之時不占中道,站立之際不堵門中。
站立時要端端正正,不斜著身子聽講。
在室內(nèi)走路不能雙臂張開。和別人坐在一起不要橫起胳膊。給予別人東西時,對方站著就不用跪著;對方坐著就不宜站起來。
將走近就坐的席位時,面色要保持不變,用兩手提起衣裳,使衣裳下擺離地一尺。衣裳不要掀動,腳步不能顯得急促。
與天子、國君相處時,站立時要讓上身向前屈,達(dá)到磬折垂佩的程度。如果君主直立,腰佩倚靠著身體,那么臣子要讓腰佩懸垂下來;君主腰佩懸垂下來,那么臣子要讓腰佩垂到地上。也就是說,這個佩垂代表了極度的卑下,但還不如“佩委”,那簡直就是趴在地上,已經(jīng)不屬于立的范圍。
古人站立的禮節(jié)很多,最常見的有恭立、肅立、卑立等。
“恭立”,就是恭敬的站立,表示對長者的尊重。《弟子規(guī)》有:“路遇長,疾趨揖,長無言,退恭立。”這里告訴我們,弟子在路上遇到長輩,要趕快趨步向前行揖禮,長輩沒有什么告誡,就應(yīng)后退恭立。這是一種恭敬。
“肅立”,就是恭敬肅穆地躬身站著,即俗語所說:不可嬉皮笑臉。漢賈誼《新書·容經(jīng)》:“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jīng)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肅立。最關(guān)鍵的要領(lǐng)是彎腰,而且彎的角度很大。大到什么程度?賈誼用“磬折”來比照。磬,是古代的一種打擊樂器,多用玉石打制。其上部穿孔,用來懸掛。自西周以后,其背部開始做成彎折形狀,彎曲的角度為“倨句一矩有半”。
“卑立”,是表示謙恭的一種站立姿態(tài)。漢賈誼《新書·容經(jīng)》:“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卑立,賈誼對此的要求是“垂佩”,佩是古人掛在衣帶上的飾物,多用玉制,系繩很短。要讓佩下垂,勢必要盡可能地彎腰。而且,比照肅立的恭敬程度,這個彎??腰應(yīng)當(dāng)超過磬折的程度,已經(jīng)不是一般的恭敬謙虛,而是卑下了,所謂的“卑躬屈膝”了。
站立本來是人最基本的自然姿勢,透露著一種靜態(tài)的人體之美,可經(jīng)過等級社會的改造,扭曲了人格尊嚴(yán),成為變態(tài)式禮儀,這是我們今天要摒棄的。當(dāng)然,今天的我們在站立時,應(yīng)該保持自信的同時,也應(yīng)不失儀態(tài)的莊重。
三、走路的禮節(jié)
古人對行走的步伐非常重視,故有了行走的禮節(jié)。
《禮記·曲禮》規(guī)定:
“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帷簿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zhí)玉不趨。”
這些都是關(guān)于走路的規(guī)定,初看時或者覺得太煩,似乎連走路都不自由。實(shí)則不然。“武”即足跡。堂上地方小,宜于小步走,“接武”,即一個腳印挨著一個腳印,不要大步。“布”即分布,“布武”即腳印不相連接,也就是放開大步走。
《釋名》載記:“緩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可以看出,趨的步伐頻率介乎走和跑之間,大可認(rèn)為是謹(jǐn)慎地小步快行。在他人面前趨,是對對方尊敬的表示。如果自己在帳幕之外,對方在帳幕里頭,彼此見不著,自然不必趨。堂上的地方小,不可能趨;手里捧著玉為什么也不趨呢?玉是貴重物品,執(zhí)之應(yīng)該小心翼翼,萬一趨得不穩(wěn)會把玉摔壞,因此執(zhí)玉時可以不趨。
《論語·鄉(xiāng)黨》載記魯國國君召孔子去接待賓客時,孔子“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趨進(jìn),翼如也。賓退,必復(fù)命曰:‘賓不顧矣。’” 孔子出使別的諸侯國時“執(zhí)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zhàn)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此篇,大量素材描述了孔子容色言動、衣食住行的行為舉止,為我們了解彼時的行走禮儀提供了詳實(shí)的動感畫面。
這里我們應(yīng)該看出,行走的禮儀很早就以出現(xiàn),至少在孔子時代的春秋時期就已完備,一直延續(xù)到清末民初,有些至今猶存。
古人也十分講究步行之美,以此體現(xiàn)人的性格情趣和風(fēng)度教養(yǎng),顯示出一種莊重和諧的美。古代常常以右位、前位為尊,故而在道路上行走,男子多右行,女子則左行;與長輩出行,小輩在后隨從,不可走在前頭;與平輩朋友出行,須謙讓并行,不得超速領(lǐng)先。
《禮記?玉澡》中說:“疾趨則欲發(fā)而手足毋移。”在平時行走的時候,直行則開快步,但是身體不能一搖一擺,因?yàn)榘凑斩Y節(jié)的要求,手肘是不能搖的,腳步是要平直的;“行容惕惕、廟中齊齊。”對平時和宗廟走路姿態(tài)都有不同要求,平時走在道路上,態(tài)度要從容自得,在宗廟中容態(tài)要莊重嚴(yán)肅。后世的《千字文》也說:“矩步引頸,俯仰朝廟,束帶矜莊,徘徊瞻眺。”走路要有規(guī)矩,頭要抬胸要挺,身體要挺拔,頭頸要挺直,一低頭一抬頭,要如同在朝廟中一樣莊重,穿著要齊整,行走時要目視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