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孟祥才(1940年——)男,漢族,山東臨沂人。彭門創(chuàng)作室導(dǎo)師,山東大學(xué)儒學(xué)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思想史的教學(xué)與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齊魯書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傳》《孟子傳》《秦漢史》《先秦秦漢史論》《先秦人物與思想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續(xù)集》《梁啟超評傳》《王莽傳》《中國古代反貪防腐術(shù)》《齊魯傳統(tǒng)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漢代的星空》《漢朝開國六十年》《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秦漢卷》《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秦漢卷》《山東思想文化史》《秦漢政治思想史》等個人專著32部,主編、合撰、參編著作31部。有關(guān)著作曾獲得國家圖書獎、國家社科規(guī)劃項目一等獎、山東省社科著作一等獎等多種獎項。在《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大眾日報》《炎黃春秋》《文物》《文藝報》《中國史研究》《歷史教學(xué)》《文史哲》《東岳論叢》《山東社會科學(xué)》《齊魯學(xué)刊》《史學(xué)月刊》《江海學(xué)刊》《人文雜志》《史學(xué)集刊》《孫子研究》等報刊發(fā)表論文300余篇。兩次獲得“山東省專業(yè)技術(shù)拔尖人才”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兼任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秦漢史學(xué)會副會長、山東省歷史學(xué)會副會長、山東大舜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孫子研究會副會長和北京師范大學(xué)、山東師范大學(xué)、青島大學(xué)等校兼職教授。

?孟祥才先生
魯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是周公,他姓姬名旦,是文王的第三個兒子(也有人認為他行四),武王姬發(fā)的弟弟。他曾協(xié)助武王興兵伐紂,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周朝建立第二年,武王去世,成王幼小,周公攝政。此時,他肩負的是治理這個新建王朝的千斤重擔(dān),面對的是十分嚴峻的政治形勢:主少國疑,周朝貴族內(nèi)部矛盾重重,一些人懷著貪婪的野心覬覦他手中的權(quán)力;被推翻的殷朝殘余在東方還有強大的潛在勢力,他們不甘失敗,伺機蠢動;周朝由偏在西方一隅的小國驟然代殷而成為整個中原的主宰,百廢待興,百事待理,真正立下牢固的基礎(chǔ)還必須解決許多棘手的問題。果然,武王死后不久,周貴族“三監(jiān)”就與紂王之子武庚勾結(jié)起來發(fā)動了武裝叛亂。一時烽煙滾滾,整個東方非復(fù)周朝所有。面對這種形勢,周公沉毅果決,舉兵東征,血戰(zhàn)三年,克殷踐奄,消除了對周朝最大的武力威脅。之后,他營建東都洛邑,大力推行分封政策,在比殷朝更大的范圍內(nèi)鞏固了周朝的統(tǒng)治。進而,他損益殷禮,“制禮作樂”,完善了周朝的各種制度和典則。他損益殷人的天命思想,提出了“敬德保民”“明賞慎罰”的新的統(tǒng)治思想。七年之中,他駕駛著周王朝這只奴隸主貴族的航船,溯激流,越險灘,沖破道道阻障,戰(zhàn)勝重重困難,將其導(dǎo)入順利發(fā)展的坦途。七年之后,周公又毅然“復(fù)子明辟”,南面稱臣,把權(quán)柄交給已經(jīng)成年的成王姬誦,表現(xiàn)了奴隸主貴族的“大公”和氣度。在他的治理下,周初的“成康之治”以中國古代著名的“盛世”載入了史冊,周公也被戴上中國古代大“圣人”的桂冠,同時作為儒家“道統(tǒng)”的重要傳人,享受后世綿延不絕的頌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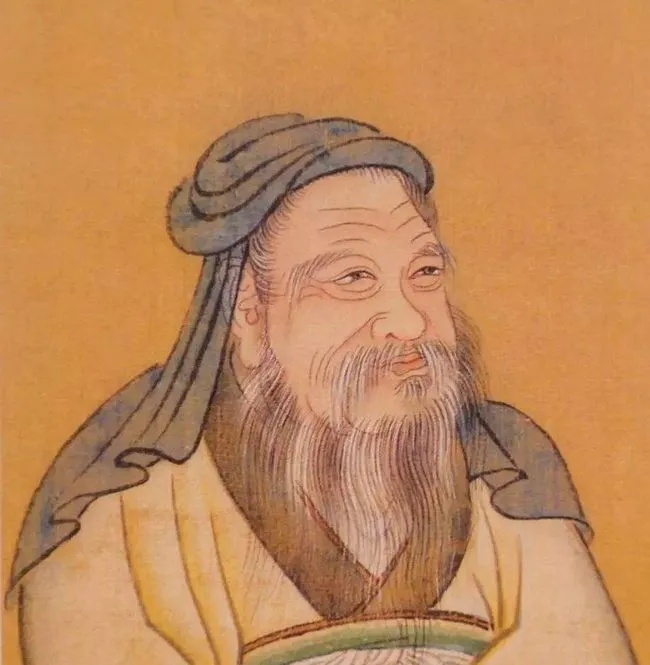
?周公
周公的思想是在損益殷人思想的基礎(chǔ)上有所創(chuàng)新而形成的。周公是一個天命論者,他的天命思想是從殷人那里繼承來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在殷人那里,“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因而敬帝和尊祖就合二而一了。殷王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兒子,他的使命是代上帝行使其在人間的統(tǒng)治權(quán)。所以,只要得到上帝的認可,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大量出土的殷墟卜辭向人們展示了殷朝統(tǒng)治者的思想面貌:他們凡事問卜,把卜兆作為自己活動的重要依據(jù)。例如,問年成的豐歉:“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問戰(zhàn)爭的勝負:“伐方,帝受(授)我又(佑)?”問筑城的吉兇:“王作邑,帝若(諾)。”等等。因而,溝通人神關(guān)系的巫、祝、卜、史在殷朝也就成為權(quán)力顯赫的官員。殷朝統(tǒng)治者不太講究懷柔政策,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用棍棒和斧鉞驅(qū)趕奴隸從事非人的勞動,以及把他們像牲畜一樣地趕上神圣的祭壇和埋入墓坑。由于經(jīng)常征戰(zhàn)保證了奴隸的來源,在殷人那里的確看不到從任何角度出發(fā)的對奴隸的愛護。到紂王統(tǒng)治時期,階級矛盾已激化到極點,“小民方興,相為敵仇,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連微子啟之類的殷貴族都預(yù)感到殷王朝末日的來臨,勸紂王收斂一下自己的兇暴和貪殘。但紂王以“我生不有命在天”為根據(jù),我行我素,作惡如故。這表明,紂王直到走上斷頭臺的前夕,還保持著對上帝的篤信,把上帝看成自己權(quán)力的守護神。在他看來,上帝既然昔日把統(tǒng)治人間的權(quán)力交給了殷貴族,今天自然也會保護自己度過任何難關(guān),使殷人的統(tǒng)治億萬斯年地持續(xù)下去。周公從殷人那里繼承了對至上神的崇拜。這個至上神,殷人一直稱帝,周人則更多地稱天。在周公眼里,天依然是有意志、有感情、君臨人間、明察秋毫、賞善罰惡的人格神,自然界的風(fēng)晴陰雨,電閃雷鳴,地上王朝的興衰更迭,個人的生死禍福,都被天主宰著。周公并沒有對天的神力發(fā)生懷疑。無論對殷頑民、方國首領(lǐng),無論對殷頑民、方國首領(lǐng),還是對周貴族,他都大講天的威力,稱頌祖宗的神靈,獻上虔誠的頌歌。如在武王率兵渡河攻殷時,“祥瑞”屢現(xiàn),周公欣喜若狂地大叫:“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武王生病時,他偷偷跑到祖宗的靈前哀告。愿以身代武王死。并說自己“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其后,在大量的文告中,周公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地向殷遺民、周貴族和方國首領(lǐng)說明,夏、殷兩朝的滅亡是由于“天命不易”,周王朝的興起更是“受天明命”,一切都是出于上天的無情安排: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天命。”
顯然,周公作為一個真誠的天命論者,他對天的威靈是篤信不移的。他并不是像有些學(xué)者所論斷的那樣,在殷人面前是天命論者,在周人面前就懷疑天命的存在。因為在周公所處的時代,上天的威靈還禁錮著所有人的頭腦,無神論產(chǎn)生的條件還不具備。與周公同時的人物中,找不出一個無神論者。“沒有人能夠真正地超出他的時代,正如沒有人能夠超出他的皮膚。”即使周公這樣杰出的思想家,也無法擺脫歷史條件的限制。不過,周公的天命論與殷人相比又有明顯的不同。第一,他把殷人上帝與宗祖神合一的一元神論改造成上天與宗祖分開的二元神論;第二,他用“以德配天”說首創(chuàng)天人感應(yīng)論。盡管這些區(qū)別還沒有突破宗教神學(xué)體系,但與殷人的天命論相比卻是一個不小的進步。這是因為,周公的上天宗祖二元神論在事實上疏遠了人間和上帝的關(guān)系。周公把上天打扮成一個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的“公正”之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一個當權(quán)的統(tǒng)治者使上天滿意的唯一辦法,不在于祭祀的準時和祭禮的隆重,而在于能夠“敬德保民”、“明賞慎罰”,把地上的統(tǒng)治搞得有條不紊:貴族內(nèi)部融洽和睦,被奴役的小民也安于奴隸的地位不進行反抗。周公的上天、宗祖二元神論雖然還不是無神論,但他引導(dǎo)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人事方面來,把事神的虔誠與事人的競競業(yè)業(yè)結(jié)合起來,無疑能夠縮小天命鬼神的傳統(tǒng)領(lǐng)地,客觀上是向無神論的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