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1940年——)男,漢族,山東臨沂人。彭門創作室導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齊魯書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傳》《孟子傳》《秦漢史》《先秦秦漢史論》《先秦人物與思想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秦漢人物散論續集》《梁啟超評傳》《王莽傳》《中國古代反貪防腐術》《齊魯傳統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漢代的星空》《漢朝開國六十年》《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秦漢卷》《山東思想文化史》《秦漢政治思想史》等個人專著32部,主編、合撰、參編著作31部。有關著作曾獲得國家圖書獎、國家社科規劃項目一等獎、山東省社科著作一等獎等多種獎項。在《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大眾日報》《炎黃春秋》《文物》《文藝報》《中國史研究》《歷史教學》《文史哲》《東岳論叢》《山東社會科學》《齊魯學刊》《史學月刊》《江海學刊》《人文雜志》《史學集刊》《孫子研究》等報刊發表論文300余篇。兩次獲得“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秦漢史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山東大舜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山東孫子研究會副會長和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青島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孟祥才先生
周公還用“以德配天”說在中國歷史上首創了“天人感應”論。殷人雖然凡事問卜,以卜決疑,但僅此并不能構成“天人感應”論。因為卜兆的吉兇與殷王的德行和作為沒有直接關系。在殷人看來,上帝和宗祖對他們的鐘愛完全是無條件的,所以天人之間也就不存在彼此“感”和“應”的關系。在周公發明“以德配天”說之后,“天人感應”才算正式成立。他第一次將天的好惡與地上人的行為聯系起來,倡導“修人事以應天命”。他一方面承認天是監臨下民、賞善伐惡、公正無私的人格神:“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臨在茲。”另一方面又認為天不是喜怒無常地隨意降下幸福或災禍。人間帝王敬德保民,天便降下福風惠雨,保佑他國泰民安,五谷豐登;人間帝王背德虐民,天便降下水旱災異,收回他的統治權力,更易新主。天的意志通過“祥瑞”或“譴告”下示人間。人間帝王亦可通過祭祀向上天申述己意,通過實際活動表示自己的赤誠。如此天人交感,構成人間的歷史運動。在《尚書·多方》中,周公正是用“天人感應”解釋了夏、商、周三朝的更替:
“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菲天庸釋有夏,菲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后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按照周公的“天人感應”論,天命對于人事的左右并不是絕對不可移易的,人的活動在天命面前也不是全然無能無力的。這實際上等于承認了人可以有條件地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樣一來,周公就在殷人僵死的天命論體系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給人的主觀能動性爭得了一個活動的地盤。對于統治者來說,其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就是通過“敬德保民”使上天認可和保佑自己在地上的統治權力。顯然,周公是用“敬德”改造了殷人的天命論。以周公為代表的周朝統治者從殷亡周興的現實變革中認識到,昊天上帝并不是將它的鐘愛一勞永逸地傾注給某個家族。“天棐忱”,“天畏棐忱”,“天不可信”,“天難忱斯,不易為王”,這些話雖然還不能說周公已經懷疑了天的威靈,但卻表明他已經意識到不能無所作為地靠上帝的恩賜過日子。為了使上天永遠將鐘愛傾注于周邦,就必須以“敬德”討它的歡心。周公認為,有德是取得天帝對地上統治權認可的最重要條件。殷人前期和中期的統治之所以比較穩固,就是因為殷的名王成湯、盤庚、武丁等德行高尚,使遠者來,近者悅,上帝賜福,神人共慶。周人能代殷而王,關鍵是“丕顯文王”德行醇厚,結果是上帝鐘愛,小民敬畏: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調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相反,夏殷所以喪失政權,主要原因就是夏桀和商紂“失德”,“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在周公眼里,,有德和天命永遠是聯在一起的,在形式上,天命雖然還是至高無上,但在實際上,有德卻成為天命的依據和前提。如此,法力無邊的天命在事實上遇到了限制。為了使周的統治永遠繼續下去,周公幾乎在每個場合都宣揚“以德配天”的理論,并以此諄諄告誡他的侄子成王、兄弟康叔、君奭以及百官、殷后和各方國的首領。“敬德”實在是周公天命思想的重要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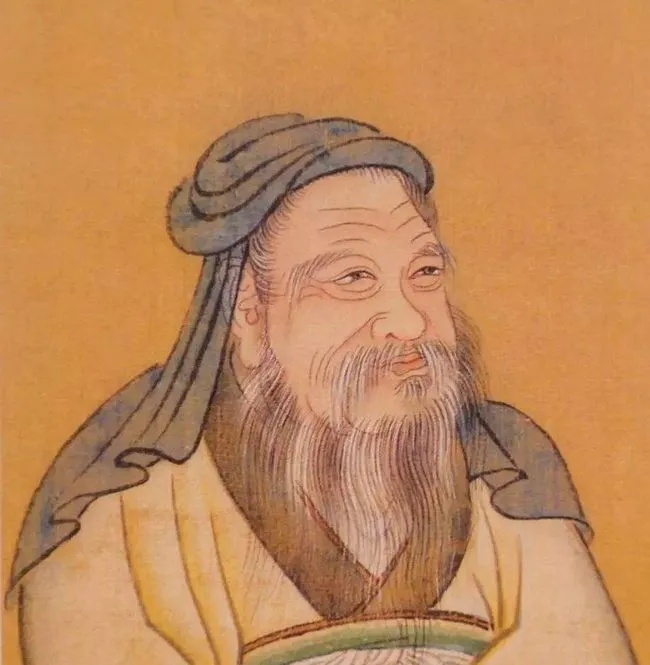
?周公
從“敬德”出發,周公要求周貴族時時以夏殷“失德而亡”為鑒戒,“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兢兢業業,小心翼翼地操持自己的政柄,要“永念天威”,對上天懷著真誠的崇敬心情;要“迪惟前人光”,永遠牢記祖宗創業的艱難,做克肖祖宗的孝子賢孫,發揚光大前人不朽的勛業。為此,就必須時刻抑制自己的欲望,像文王那樣“克自抑畏”,那樣“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要“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不要貪圖安逸,不要大興游觀,不要無休止地田獵,更不要聚徒狂歡。周公這種要求以國王為首的周貴族克制自己的欲望、加強修養、在道德上做萬民表率的思想,比之殷貴族那種兇橫殘暴、肆無忌憚的嗜殺縱欲來,是有進步意義的。事實上,在周公的大力提倡下,更由于當時階級斗爭條件的制約,周初的幾代統治者都比較注意抑制自己的欲望以緩和階級矛盾。“成康之治”與統治階級相對不太荒唐是有直接關系的。從“敬德”出發,周公在中國歷史上較早地提出了“任人唯賢”的主張。要求“繼自今立政”,必須堅決擯棄無德無才的“ 人”,選取“克明俊德”、智能卓著的“吉士”、“常人”,從而達到“勱相我國家”、“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的目的。從“敬德”出發,周公還提出“保民”和“慎刑”的主張,要求統治者了解廣大奴隸和平民的處境,“聞小人之依”“知稼穡之艱難”,關心他們的疾苦,使他們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溫飽生活。要“庶獄庶慎”,有條件地運用“刑殺”,使其與懷柔政策起到相輔相成的作用。
“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貫之”的周公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比他的前輩貢獻了許多新的東西。他第一次在殷人無所不包的天命思想體系上打開了一個缺口,給先秦天道觀發展史帶來了有意義的轉折;他第一個發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用,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論;他第一個看到了奴隸和平民的偉大力量,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敬德保民”思想。在中國奴隸社會還處在蒸蒸日上的發展時期,周公作為朝氣勃勃的奴隸主階級的一個代表人物,以他巨大的政治建樹和卓越的思想創造,促進了這個社會的發展。他無疑應該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
由周公所開啟的魯學比較全面地移植了周朝的禮樂文化,它極力維護宗周文化的純潔性,特別重視道德名節和傳統文獻闡發的宗法倫理觀念。正是這樣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氛圍,孕育了儒家學派和它的偉大創始人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