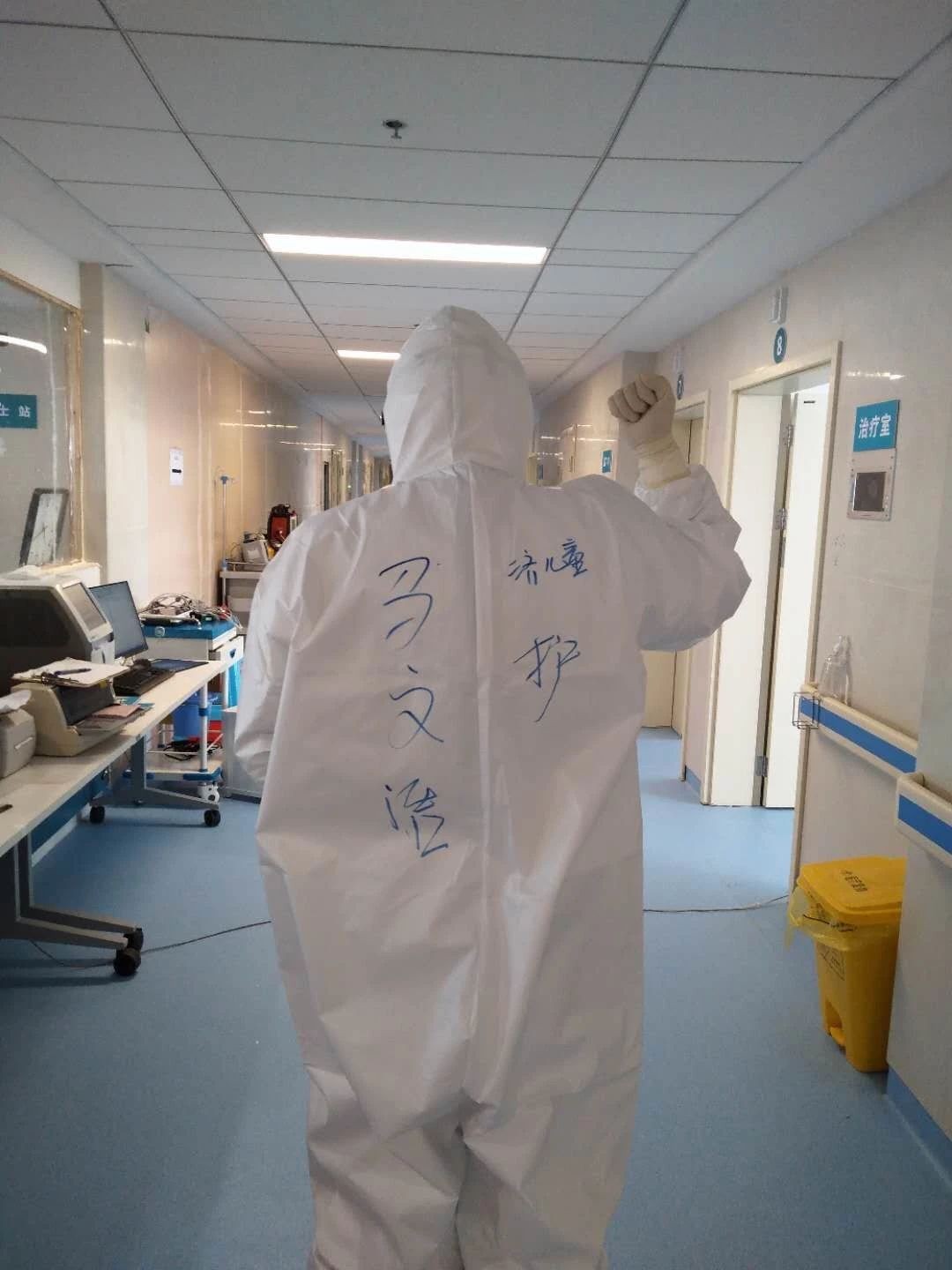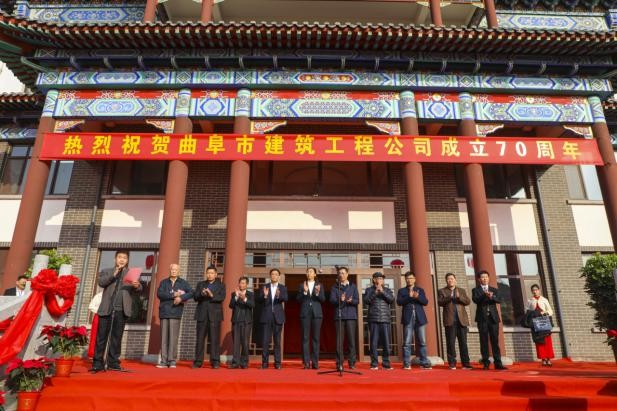楊朝明:孔子“天下為公”思想的時代意義
楊朝明:孔子“天下為公”思想的時代意義
本文轉載儒行楊朝明文章

孔子“天下為公”思想的時代意義
年終考評時,如果你的評語有“此人自私”或“私心較重”之類的評價,你一定十分不爽。這個大家都不喜歡的“私”其實與“公”相對,人不自私,就要有公心。人們都屬于特定的社會關系,就要考慮自己的社會性存在,那么,心里裝著“公”,具有公德意識就很有必要。孔子說“天下為公”,正是希望人們不要自私,做一個合格的社會人。
孔子的社會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話正應了“公道”那個詞,只有“公”,才有“道”;沒有“公”,“道”何求?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人的社會聯系主要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個方面,處理好這些關系十分重要,所以《中庸》說:“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社會中的其他關系都由這些關系派生出來。處理這些關系,需要努力修身,人人有“道”,這個“道”就是孔子的恕道,即推己及人、換位思考。主動修身的人越來越多,社會就會有公道。
在孔子和早期儒家那里,“公”是處理各種關系的基本原則,其內涵和外延都很豐富。歷史上,很多人論證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的關系,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應當遵守社會的規范,這些都可以包含在“公”的概念之內。作為社會的人,人不能只考慮個人,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角色的要求,這才算做到了“公”,才符合“道”的要求。孔子希望社會精英們“志于道”,有更多的人遵“道”而行,工作中“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敬”,家庭中“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社會上“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果是這樣,距離孔子所理想的“天下為公”、社會“大同”就不遠了。

長期以來,在不少人心目中,“天下為公”好像只是一個高尚的口號,甚至是可望不可即的空想。其實,“天下為公”應該具體落實為人們切實的行動。孔子有他心目中的“天下為公”,那就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為人”,“奸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人們敬老愛幼,安居樂業,有充分的社會保障,不浪費,不私藏,安分盡力,人心和順,社會安寧。做到這些,需要人們的公共意識,需要人們的社會性意識。而這,不該是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乃至一個集體都希望做到的嗎?這不也正是我們追求的理想狀態嗎?
星云大師在他的《人間因緣》中有“一半一半”的說法,他說“善良一半,邪惡一半”、“真的一半,假的一半”、“佛的世界一半,魔的世界一半”。這樣說來,“公”與“私”也是一半一半,自古及今,人們的心里都有“人心”與“道心”、“人情”與“人義”、“天理”與“人欲”的對抗,早在殷末周初,姜太公《六韜》就說“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這種“欲”與“義”、“敬”與“怠”的斗爭經常會出現,它有時就表現為“公”與“私”之間的斗爭。《尚書》說“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墨子》提倡“舉公義,辟私怨”,哪家哪派都希望“努力好的一半,減少壞的一半”。人屬于社會,就理應考慮自己屬于一個家庭、社會或集體、國家,人自然不能總是想一己之私。社會要更加美好,人們就要努力“公”的一半,減少“私”的一半。
如何增長公共意識,提升公共道德?孔子提出的方法是循禮而動。他說:“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治之?”“禮”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規則、規范,是標準、界限,是公德的要求。“天下為公”的“公”也可理解為“共”,人生活在共同的社會中,就應有明確的“社會性”意識,從而休戚與共,協同合作。應該摒棄自私,互相關心,扶危濟困,而不能各行其是、自私自利,更不能損人害人、弱肉強食。“天下為公”的觀念啟示人們要有“社會共同體”或“命運共同體”意識,多包容,善合作;少對立,不對抗。
(圖文編輯人:何暢儀)
(編者按:本文原題目為“不忘公心,做社會人”,發表在《孔子的叮嚀》,山東友誼出版社2019年出版)

-
點擊次數: 2682024 - 03 - 09社區里的孔子學堂讓文化走“新”入“心”由中國孔子基金會組織發起的“孔子學堂” 落戶濟南舜耕街道辦事處舜華社區,這是全國首家“孔子學堂”,也是中國孔子基金會孔子學堂公益文化品牌項目建設的起點。目前,孔子學堂遍布全國各地及海外17個國家和地區,總數達3300家。“孔子學堂能把大家集中到一起,用文化吸引居民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來,這對于基層治理是很有益的。”志愿者張瀟說,新的一年,他們打算把學堂建設和當地的舜文化進一步結合起來,讓文化資源、文化傳承人發揮優勢,“傳統文化的弘揚和創新絕對不應該局限于一時一地。以孔子學堂為載體,我們要讓自己的文化走出山東、走出國門,把傳統文化用更多更好的形式講給大家聽。”社區孔子學堂守護基層的文化溫度,在舊歲新年交替之際,為社區群眾搭起文化傳承的橋梁,讓傳統文化在此代代接續、薪火相傳。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廉潔品牌入選省直機關近日,省直機關紀檢監察工委印發了《清廉致遠——省直機關廉潔文化建設工作品牌》一書,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廉潔文化品牌成功入選。此書是為了展示省直機關廉潔文化建設成果匯編而成,收納了23個省直部門廉潔教育陣地,38個廉潔文化工作品牌、19項廉潔文化建設特色工作。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入選的工作品牌有“清風儒家 謙謙君子”廉潔文化品牌、孔子博物館“文物話清廉 鑒古沐清風”廉潔文化品牌,孔子博物館廉潔教育體驗基地入選陣地建設欄目。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將以此次省直機關廉潔文化建設成果展示為契機,加強學習交流,繼續深入推進廉潔文化建設,教育引導黨員干部從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線,為“清廉山東”廉潔文化品牌建設貢獻力量。
-
點擊次數: 2102024 - 03 - 04《走進孔子(中英文)》建設座談會召開為提高辦刊質量、擴大刊物影響力,3月2日,由孔子研究院主辦、《走進孔子(中英文)》編輯部承辦的《走進孔子(中英文)》期刊建設座談會在孔子研究院召開。特邀專家、期刊編輯委員會代表圍繞拓展優質稿源渠道、進一步提升期刊影響力展開交流探討。大家充分肯定了《走進孔子(中英文)》在過去兩年中取得的成績,并圍繞貫徹落實“兩創”要求,就刊物定位、欄目設置、進一步提升海內外影響力等方面相繼發言,希望刊物可以在未來發展中進一步明確辦刊方向、體現時代精神、注重傳播創新,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與普及工作。“青瓷百詠”特展在浙江開展 3月3日,“如瓷·出色”百名非遺傳承人“青瓷百詠”暨青瓷文創特展在浙江展覽館開展。此次展覽以蘭花為主題,由100名青瓷非遺傳承人創作100件青瓷蘭花作品,將非遺文化與家風文化相結合,展現“瓷蘭氣韻、君子如蘭”的文化氣息和“耕讀傳家、孝廉傳世”的厚重家風。 此次展覽主題為“青瓷百詠”展。100名青瓷大師把以“蘭”為主題的百首詩詞、百幅書法、百幅繪畫、百方印章、百幅拓片作為素材,二次創作出100件青瓷作品,托物言志、以文化人,創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同時,展覽還平行展出“蘭花百詠”詩書畫印,即以“青瓷百詠”作品為素材,由來自全國的實力派名家創作100首詩詞、100幅書法、100幅繪畫、100方印章、100幅拓片,以工藝美術的創新轉換實現跨文化、跨區域的交流表達。 展覽總策劃、《家風·孝道》系列叢書主編韋一介紹,“青瓷百詠”項目是該叢書繼“孝道百詠”“蘭花百詠”“天使百詠”等文化工程后推出的第四個“百詠項目”,旨在將青瓷文化、蘭花文化、家風文化巧妙融合,更好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
點擊次數: 2442024 - 02 - 25溫陽鄉校大成殿重修竣工儀式舉行2024年2月24日,韓國孔子文化中心總裁樸洪英一行出席了溫陽鄉校大成殿的重修竣工儀式。與會者包括國會議員李明洙、牙山市市長樸慶貴、牙山市議會議長金熙英等相關人士,以及該地區儒林百余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經94歲高齡的成均館元老、溫陽鄉校前任典校、牙山的精神支柱李興馥會長,盡管身體尚未完全康復,但在樸洪英總裁及在場眾人的攙扶下,也出席了此次儀式,為在場來賓以及儒林眾人帶來了感動與鼓舞。溫陽鄉校建立于朝鮮時代,經歷了壬辰倭亂的大火摧毀,于1610年重建至今。在1982年,曾進行過一次對大成殿和明倫堂的重修。此次大成殿的修繕工程于2023年5月啟動,最終于2024年1月底竣工。 “龍經濟”活躍濟寧文旅市場龍年春節,孔孟之鄉山東省濟寧市迎來眾多游客,文旅市場紅火。古運河從濟寧穿城而過,大年初一,新年首趟龍船搭載著百余名游客向龍拱港進發,開啟新春“尋龍之旅”。龍拱港依運河支流龍拱河而建,相傳遠古時期有巨龍從天而降,拱出一條溝壑,行云布雨,水流溢滿成河,從此旱魔降縛,災民得救。游客乘船找尋古老的傳說,祈福龍年風調雨順。春節期間,濟寧每天舉辦多場文旅活動,為中外游客奉上文化大餐。曲阜孔府過大年暨明故城夜游活動吸引了眾多游客,三孔景區“尋龍”“漢服秀·游三孔”、孔府皮影春節專場《年寶大賀歲》等活動精彩紛呈。“‘龍經濟’背后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我們對今年濟寧文旅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濟寧市委主要負責人表示。
-
點擊次數: 2242024 - 02 - 25孔子博物館春節開放活動圓滿收官龍年春節,博物館熱度持續升溫。孔子博物館按照全省2024年春節文化和旅游行業安全生產和假日市場工作的部署要求,多措并舉,開展“博物館里過大年”系列活動,做好假期開放服務保障,春節開放工作在安全祥和的氛圍中圓滿收官。節日期間,孔子博物館累計接待觀眾89851人次,單日最高接待量達17011人次,已然成為“東方圣城、孔子故里”的熱門打卡地。孔子博物館提前研判,召開春節假期開放和安全生產工作會議,制定開放工作方案,相關部門通力協作,強化服務供給,保障節日期間運行平穩。節日期間,講解接待共計142場/次,服務觀眾1834人。從細致入微的設施維護到信息咨詢、助老助殘、母嬰關愛等貼心服務,觀眾滿意度大幅提升。新元肇啟,華章日新。孔子博物館通過打造年節文化氛圍,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呈現給海內外觀眾,春節開放工作圓滿收官。下一步,孔子博物館將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上持續發力,以高質量的文化供給豐富群眾文化生活。“孔府過大年”文物展反響熱烈近日,孔子博物館“六合同春——孔府過大年文物展”正式開展。本展覽分為兩大部分共四個單元,第一部分龍行千年包括龍起東方和龍藏百器兩個單元,第二部分年至圣府包括兩個單元,即第三單元敬神祭祖和第四單元歡慶祈福。通過130余件(套)館藏文物講述年味里的中華文化。在文物展覽的同時,孔子博物館配套開展豐富多彩的社教活動,如蒸壯、寫春聯、印門神等。同時“黃河文化大集”上眾多的非遺技藝、美食、演藝、年貨、游戲、民俗體驗等項目將集中亮相,通過親身參與和互動體驗,帶領大家一起尋找記憶中的濃濃年味,感受“春節”里的盛世中華。
-
點擊次數: 2152024 - 02 - 02甲辰年”孔府過大年“活動啟幕2月2日正值北方農歷小年,甲辰年“孔府過大年·地道中國味”啟動儀式在山東曲阜舉行,展現孔子故里山東曲阜的文化旅游資源,喚醒民眾傳統節日“儀式感”。啟動儀式上,孔廟景區內文創展、非遺展包羅萬象,20多個展位根據不同主題進行精心布展;孔府門前“福祿壽”三星向現場游客送上新年祝福;百名書法名家潑墨揮毫,將美好的祝福融入墨香之中,為市民及游客寫春聯、送“福”字。據了解,孔府自古以來就傳承著規模盛大的中華民族春節禮儀,是現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中國家庭過年模式。近年來,“孔府過大年”系列節慶活動不斷在傳承中創新發展,在保留傳統文化精髓的同時,活動形式也更加符合現代人的精神追求。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在京召開近日,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在京召開。會議強調,要加強文化精品創作生產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強調,“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著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賡續中華文脈、譜寫當代華章,充分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我們一定能夠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更好推進文化自信自強,不斷以新氣象新作為開創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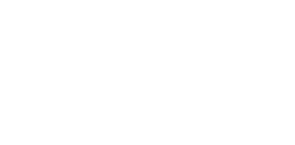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手機:13863756448 郵編:273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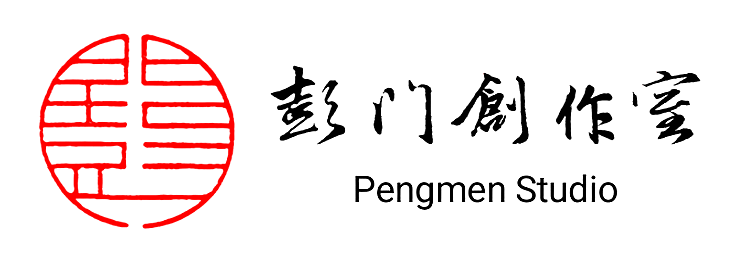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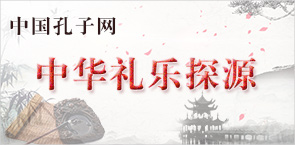





![[人民網]北上廣是挺好的,但我還是喜歡曲阜 [人民網]北上廣是挺好的,但我還是喜歡曲阜](https://0.rc.xiniu.com/g1/M00/44/61/CgAGTF2ihtCAa0puAAO3k3tehiE872.jpg)